每个事件都值得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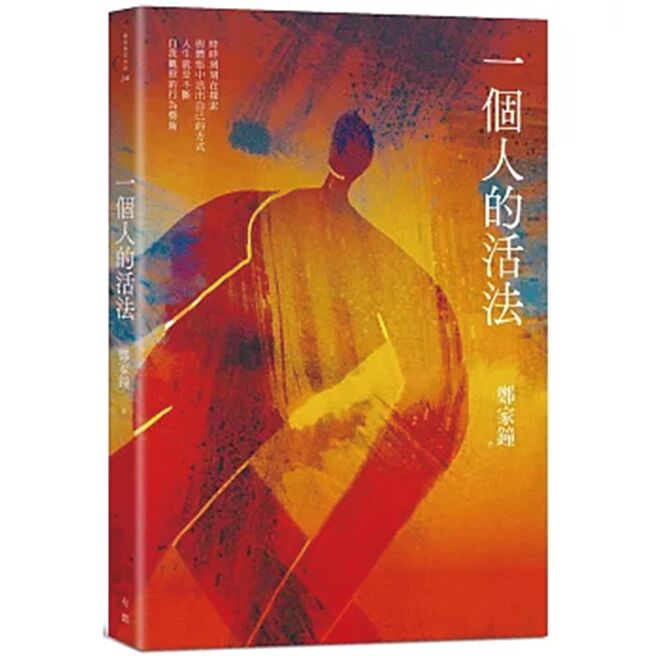
一个人的活法(有鹿文化)
2022年十一月在关渡美术馆巧遇郭昭兰老师。
她跟谢牧岐共同策展「在前卫外围的莘莘学子:从1985年素描事件出发」。
这是怎样的事件呢?其实是个美术系师生不想老是画石膏像的事件,当时若干老师倡议素描不是临摹石膏像练习,而应是自我观照的艺术表现。这个倡议后来就枝繁叶茂成为一个潮流。郭昭兰把当年老师们的绘画与装置的作品,到学生们一系列的创作变化,及现在的学生如果回到那个事件的源头─他们会如何创作?这些展品的呈现串接了北艺大由当年的素描革命,到持续演变的脉络,一直到当下的再诠释。
这成为一个既前瞻又回顾的「事件展览」,也呼应了关渡展「事件是一所学校」的主题。
郭昭兰在策展说明中说:「素描事件对我而言,无不投射着双重的青年形象:一方面是以艺术抱负投身刚结束乡土运动的台湾;另一方面则是相信单纯艺术的实践,便足以成就人生志业。莘莘学子的艺术自由与艺术理想性,已经是这里每个师生两代之间共同的桥梁。」
这意味着一个素描事件居然有这么大的系列影响,甚至变成一个学校的学风资产,自然非常有意思。
有些事件只有回看,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
我也是被事件所影响才会到今天的位置。
1970年的保钓运动,同时惊动了两岸三地的青年。当时高中生的我,本来是丙组,准备跟大家一样考医学系,毕业后想当医生的。
一直到某天受到保钓爱国热潮影响,建中学生发起罢课,在集体起哄下各班班代表齐集图书馆商议罢课的后续,身为班代的我也在其列。
当时处于戒严时期,罢工罢课形同造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更何况我们是在警备总部的鼻尖下闹事?
迅即大批军警包围建中准备冲进来抓人,我们从窗户望向门口,看到校长、老师与教官挡在门口理论,不让军警入校,这可是一种明显的抵抗,同学们一方面事态严峻,一方面危及老师,于是班代表们终止罢课,呼吁同学解散回到教室,在关键时刻弭平了这场风波。
事后,教官来到图书馆慷慨激昂的演说,直指现在优秀同学不是想当医生就要当工程师,文法组变成冷门组,想当年五四运动投入救亡图存的都是文法科学生,同学如果爱国,应该要仿效五四,进入政治、社会、法律、经济科系,别一窝蜂念甲丙组(工科及医科)。
受到当时的刺激,一群班代集体转组到丁组,我也是其中之一。从此当不成医生,最后当了记者。
保钓事件是个大事件,海内外风起云涌,建中这个「罢课未遂」事件,是历史洪流中的小插曲,但它确实影响我的一生,我当年的第一志愿就是台大经济系,以为「经济」是「经世济民」的缩写(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将Economics翻译成经济的)。
我于是成为经济系学生,然后意外进入媒体。回看这段历史,感觉到人生每个参与的事件都有它非比寻常的意义,原来,每个事件都值得深究,其与今天自己的位置息息相关。
我在这件事的学习是:
①此事促使我用三代以上的视角来看一些源头性的事件。例如一群同学的集体跳转,有些人从政,有些经商,有些是律师或立法委员,注定也会成为社会某些事件的源头。
②再如台湾的媒体发展史由戒严到解严,由垄断到恶性竞争,由过去充当文化论战旗手到现在深陷资讯操控的场景,三代的媒体人坚持了什么?这坚持能传承下去吗?还有当前媒体人的价值观转变等,都因为事件们的因缘和合而来。若要理解现况,我们需要理解「每个事件都值得深究」这个道理。
1985年的素描事件是教育事件,经过几十年,总体的教育有提出什么新方向吗?有什么事件可以推动教育转型?尤其是AI时代?
一个运动起点是个小小事件,但一个事件变成一所学校,单纯只是有人愿意把它照料好发展下去而已。
因此,我对一个有意义的事件能够踏出第一步,总是充满了期待。(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