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完全的自己─阅读古月

在写诗的路上,古月五十多年来始终如一。图/本位淬锋120x320cm(漆画)。(李锡奇作品/古月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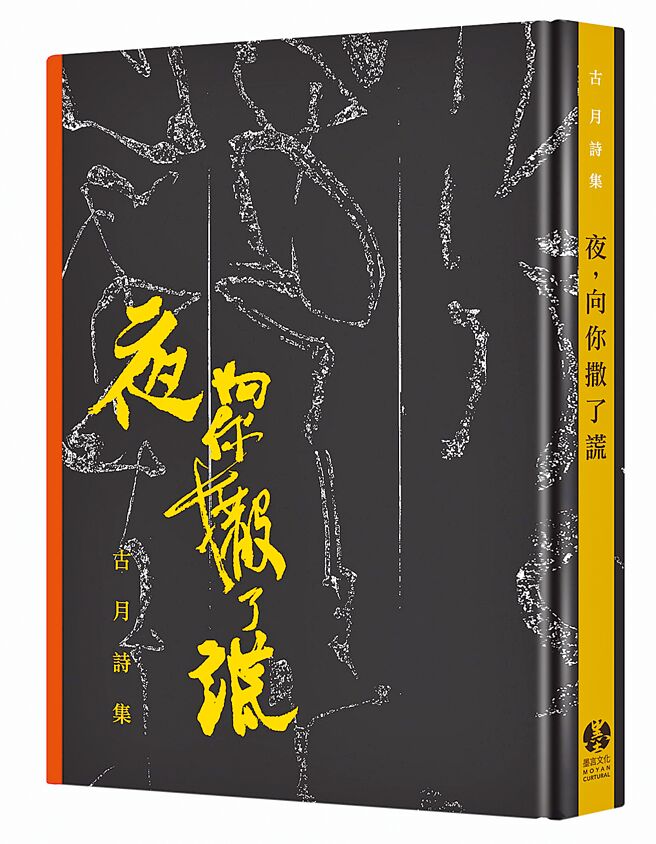
诗人古月出版新诗集《夜,向你撒了谎》(图)及《燃烧的月亮》,其中《燃烧的月亮》并有中英法语版本。(墨言出版社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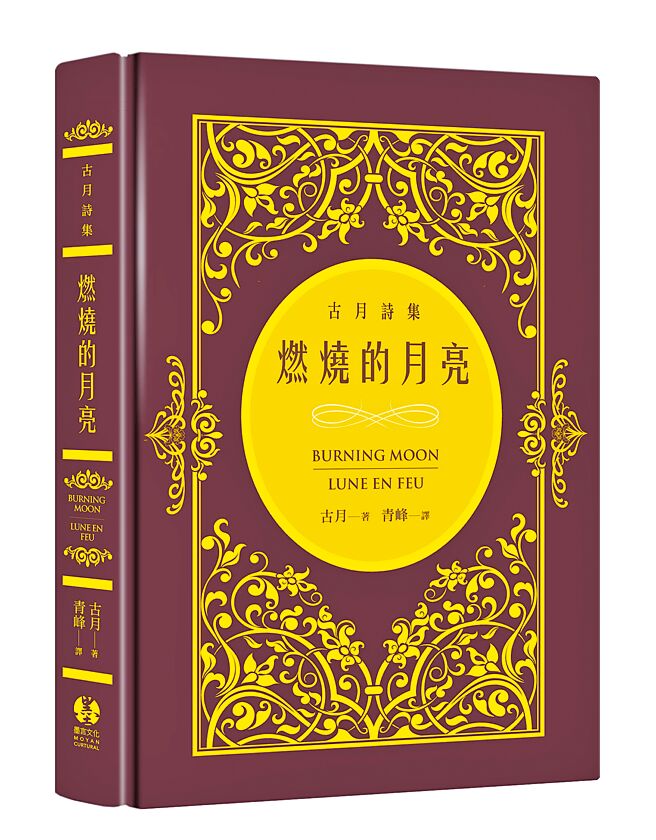
诗人古月出版新诗集《夜,向你撒了谎》及《燃烧的月亮》(图),其中《燃烧的月亮》并有中英法语版本。(墨言出版社提供)
1.如何思索一个诗人
文字里的诗,有时难以定义一个诗人。
对诗,随着年岁增长,我更了解自己的渺小,以及狭隘。也渐渐明白,看待一个「诗人」,综观会比单纯的文本分析来得贴近诗人的原型。诗人的生命态度、真实生活、对世间的心意与处世的品性,甚至对社会的涉事、悲悯与理想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完整的诗人作品的一部分。
要说诗人古月,脑海中快转、浮现许多超连结,除了文字的诗作,其实古月是多面向的──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年轻时曾以淑世济民为志,如诗之悲悯情怀;她有诗意般细腻的厨艺;丈夫是知名画家李锡奇,因此她对艺术有长期而广泛的涉猎;她写诗之外也写一手灵慧的散文;她也是作词人,我们五年级世代朗朗上口的歌,像王海玲唱的《巴黎机场》片尾曲〈我心似清泉〉,甄妮唱的〈唤山山不走过来〉、〈待月草〉,以及施孝荣〈摇橹的人〉、甫过世的刘蓝溪〈守住一窗雨〉等等。古月的诗艺内涵是多元的、也是生活的。
看待一个诗人,必须以「整体」视之。有时很难单纯以文本界说和概括。藉古月的诗〈月之芒〉来说,「水天一色/天上有水/水中有月/两相溶悦」,这个「整体」是液态的,天上人间、镜花水月皆与诗人生命中的种种相溶一起,方成诗人具体形象。
2.航向诗心
既然谈古月的新诗集,不免要回到文字诗的范畴,追索、想像,一起航向她的诗宇宙。
古月自一九六四年开始写诗,迄今超过五十载。最初经由文晓村引介,参加「葡萄园」诗社,而正式进入诗坛。彼时的她,在诗社中感受到人在异乡的温情,诗风趋写实和抒情,带有典雅灵思,以及悲悯情怀。一九八五年她加入所谓「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世纪」诗社,某部分原因可能是李锡奇的很多知交都是创世纪诗人,尤其与商禽相识最久。当时创世纪以军中诗人为主,阳刚氛围较浓,时代的辗转波折、人生的顿挫,促使他们思索生命、探究存有。古月看似柔弱,实则外柔内刚,或许精神上与创世纪诗人更契合,如同她的诗句:「迟暮的月/以水的柔软/溶于火的炙焰」。
古月最早的诗集是《追随太阳步伐的人》(1967),当时二十五岁,诗虽青涩,但有独到的女性视角和个人的宗教情怀,创世纪诗人辛郁说:「古月本就是一个长于写『情』的诗人,早年她的诗集《追随太阳步伐的人》,就充满了热烈的情感波涛,她对生命的寻求,大多从『情』着力,而深化为『爱』。」古月经常将情与爱,换喻或升华为一种宗教悲悯情怀,古波斯诗人鲁米(Rumi)在诉说苏菲教派哲学时就常透过情诗,现代歌者李欧纳.柯恩(Leonard Norman Cohen)因曾追随日本杏山禅师,所以他的音乐有时也会以情诗作为媒介传达禅思,藏传佛教喇嘛仓央嘉措的诗,亦如是。
古月的第二本诗集《月之祭》(1975,与李锡奇合著的诗画集)跟第一本间隔长达七年才出版。1969年美国太空人阿姆斯壮登陆月球是科学界大事,但对东方艺术家来说,多少作品是对月亮的想像,现在都破灭了。李锡奇跟古月讨论,「你写我画,宣布月亮的死亡。」古月写嫦娥已死:「一杯祭酒/洒向青天。」这是祭月,因为科学太先进,他们宣判月亮死了。就当时可谓前卫大胆,诗人商禽称她:「是女性诗人中少数具有宇宙视野的作家。」
古月虽与李锡奇诗画结缘,但在艺术世界里,他俩各有各的花园。古月既不想移植别人,也不太受他者风格影响,相较于李锡奇不同时期多变的画风,古月只做她自己心灵的园丁,培育自己的梦与种子。辛郁就说:「古月的诗作绝非李锡奇画作的说明。」因为古月的诗,自有画境,他说「从具象到抽象、从平面到立体、从单一到繁复、从明朗到幽深、从无色到斑缦,诗中给出了绘画的美感,是十分难得的。」这时期的古月,历经人妻人母和现实生活,诗虽一贯抒情,但明显从温柔中透出坚毅。从少女时代的多愁善感,到这时期的成熟,如她所言:「没有经验过贫穷、痛苦的爱是不被珍惜的。」
第三本诗集《我爱》(1994)更是隔了长达十九年。当然李锡奇的画与爱,某部分成为她诗花园里的养分。跨入千禧年,已届中壮年的古月作品,在抒情之外又培育出一些质地较坚硬的树种,例如写战争,取材自李锡奇的故乡金门,但树还是古月自己花园里的树;栖止于枪管上的蝴蝶,飞起来还是蝴蝶自己的样子,不会陷进别人的烟硝。古月在过往的诗中,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做完全的自己。」在新诗集中的〈说给夜来听〉一诗,古月更以「夜」自况:「夜是不羁的/以独特的节奏和文字/诠释人世之旅」。
身为诗人,古月一边做自己,一边悠悠缓缓地改变,前述战争题材、祭月之外,她也写现实性作品,例如写英国王妃戴安娜的死亡,或写在西班牙看到的斗牛竞技……这些诗透露出她内心耿介素直和入世的一面,然而并没有背离古月的本质,远远地呼应从她第一本诗集就存续的对人间之悲悯,有时近乎一种宗教的不忍情怀。
二○一○年古月将她之前的作品选录九十余首,命名为《浮生》出版,里头全是她的真情实意。她说:「面对广畴的环境,我只是个陌生的书写者,写我对人生追求的一种态度及看法,里面有我成长过程的欢喜与忧愁。」一直以来,古月的创作从不汲汲营营,不与世俗争逐,总是以优雅缓慢的自我节奏行进,却始终如一地行进了五十余年,可见她刚柔相济的强大韧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如同创世纪同仁管管所说:「把自己写成诗,比写诗更好。」也许古月把自己活成一首诗,比写诗更重要吧。
3.写诗就是我的祈祷
这本新诗集《夜,向你撒了谎》,相隔《浮生》十二年,十二年称为「一纪」或「一轮」,像华人世界的十二生肖一轮,代表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重新的开始。古月回顾过往的生命历程,并书写当下人生,且此诗集在丈夫李锡奇过世后出版,亦别具意义。全书收录七十余首新作,读到〈送别──致锡奇〉,百感揪心,多少荼蘼往事,盈溢着伤怀与不舍:「你已穿越回到了童年/丹青丽焰绘百川/徒留骊歌声声催唱/岂是一壶浊酒衷肠/能卸梦中清寒」。偶尔「走访你儿时的足迹」(〈得月楼的月光〉)既寂寞、也温暖,古月透过情诗,传达爱,也将爱转译,让读者思考人生无常。
【辑一.郁黑之旅】,写岁月的递嬗,写肉身的单薄,也写昔人已远,以及乡愁。她雕刻时光,用温柔的笔刀。
辑中的「怀人诗」,除了追念丈夫李锡奇,亦怀想已逝的创世纪同仁洛夫和管管两位诗人,以及古月的父亲和母亲。情意纯柔如丝绸,亲人故人已远游,明月明年何处共看?悲愁一时太巨大,心灵渴求答案,〈午后的海印寺〉一诗触及哲思禅意,她提问金面如来佛是否也有梦?每个人对生命都有未完的功课,「殿门外的莲荷亭亭/两只蜻蜓缱绻在花上/修练瑜伽」。「瑜伽(yoga)」在梵语中是「身心相应」的修持法,或许这是她对情对爱,必须修行的功课吧。
辛郁说古月:「专于用情,古月的诗便也敏感的反应了对季节的体认,刻画出在季节的递变中一个女子的心灵活动。」【辑二.秋风吹散多少空寂的灵魂】恰恰暗合辛郁所言,古月借由此辑回溯、贯通之前作品的一致性。在【辑二】中她以秋季的节令开场,自秋诗篇篇,进入冬之小雪大雪,再回到流苏与苦楝的春日。她延续【辑一】岁月的沧桑基调,「落笔/全是光阴的留痕」,然而她添加了季节的旋律(尤其是缤纷善感的晚秋光谱),那乐音、那颤动、那起伏从大自然之万籁汇流到一颗诗心,且歌且回旋,弹指间,她「企盼一个指尖的温度/抚慰寂寞的灵魂」。渐渐悟得「写诗来自于灵魂」、「诗是灵魂的代言」、「山花寂静/处处都是诗」,灵动字语、抒情韵脚穿梭于晚秋人生。
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内心斑斓活跃的古月,她有时化身漫山枫叶,有时又变成一只小甲虫「以孤独又炽热之姿/向那片雨后湿濡的叶子/裸裎心事」。她时而绽放热情、时而品味孤寂;她时而近观自我、时而放眼天涯。
晚秋萧瑟,却同时呈示色彩的繁华。爱过、伤过、苦过、忍过而来到某个年纪,突然醒悟一切孤独都有裂缝,光会从那里进来,照亮并温暖「我的春天/我的梦」。
古月的诗,大抵属中国抒情传统,兴观群怨、诗画情景交融、诗乐互相应唱。她的写诗时代,正好历经台湾现代诗「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之论争与抗衡,古月比较像是「纵的继承」,但更真确地说,她的抒情传统不是诗学理论的抒情传统、也不是受时代风潮影响而来的,而是骨子里的脾性就是如此。
【辑三.空笑梦】是古月的「涉事」或「涉世」。有旅行诗,例如她到中国贵州、安徽、北疆、海南岛,她至印度,她在台湾淡水、台中等驿踪行脚。如泰戈尔所云:「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达到最深的内殿」,她的旅行诗往往不是注记欢乐,而书写悲悯,譬如写北疆,「野草漫山染成枯黄/几棵颓朽的林木/像无家可归的老人」。
这些「旅行诗」可以参读【辑一.郁黑之旅】中写离岛的长诗〈岛诗三唱〉,这组诗颇具分量,「我似一棵行走的树/心若没到位/走到那都是流浪」。旅行终究还是为了内在的探索、灵思的解密,并透过「诗的箴言引渡迷津」。最终,古月要思考或提问的是「存在」的哲学问题。随着人生的拉长,涉世阅历让她在旅途之中,将生命咀嚼得更透澈。
此辑中更有一系列有关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涉事观察:「清朗的日子不再/骤然面临悬崖边缘/黑水的潮汐汹涌/肉身形成一座废墟」(〈落沙〉)。有她对第一线防疫人员的关心,也有她直言不讳地对政府的批判。这类写实题材,以前就曾在她的诗集出现,她不是爱批判的诗人,但外柔内刚的个性,偶尔有些话不吐不快,恰恰反应出她正直不阿的一面。
在诗集的最末,我们读到〈重返昨天〉,呼应诗集一开始对故人、对年华逝水的深思,「重返昨天/是谁在你的墓前/葬下了一生的许诺/昨日之日唤不醒/回望已是个陌生的影」。其实古月心中明了,人生之得与失,都值得珍藏。新诗集《夜,向你撒了谎》既有古月一本初心的真挚,更有她珍贵的人生阅历,当然也是丈夫李锡奇过世后她首次出版的新诗集,伤怀感喟也难免。我想起李贺的诗:「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对古月来说,人间既有情、亦荒凉,她愈参愈透,最复杂的情感,如今唯有诗,可以倾诉。
(古月新诗集发表会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二时三十分于台北市同安街纪州庵文学森林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