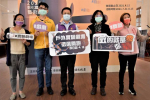舞台艺术本土化,当以世界为天中国为地
在近期举办的各种大型艺术活动中,优秀舞台艺术的本土化改编成为引人注目的潮流。《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待戈多》《哥本哈根》《探长来访》等经典作品之外,《断手斯城》《枕头人》等异域新作同样令观众满怀期待。有着深厚民族文化积淀的传统戏曲,也通过对国外戏剧作品的改编,探索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从粤剧《刁蛮公主戆驸马》、黄梅戏《贵妇还乡》、河北梆子《美狄亚》、豫剧《朱丽小姐》的先后上演,到最近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蒲剧、豫剧双版本的《俄狄王》的推出,本土化的步伐越来越大,显示了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热忱和坚守、发展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国外优秀文艺“拿来”之后,要使其适应中国国情,被中国观众接受,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改编。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中最重要的始终是它的可直接了解性,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觉到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
国外舞台艺术作品的本土化,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尽量忠于原著,保留原作的时空背景和基本的人物、故事框架,总体保持原来文化的特色,仅在形式上适当渗透中国元素,以民族性点缀普世性。上海大剧院版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在讲述“胡桃夹子和老鼠王”这个经典故事的基础上,在第二幕的“中国舞”中飞舞起一条中国龙,著名的“雪花舞”也以中国的雪山为背景,以中国元素的融入对接本土观众的审美需求。此外,本土化的语言表达、中国典故或网络梗的使用等,也是常用的手法。二是重新阐释为主,把原作的时空背景、人物、情节都进行中国化的移植和改造,以反映中国的社会现实,传达中国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如话剧《破罐记》改编自德国三大喜剧之一《破瓮记》,它虽然借用了原作的故事框架,却剔除了其文化虚无主义的寓言色彩,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中国的北宋,以中国式的人物和情节诠释官场的复杂生态、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微妙关系,表达了对清明政治的向往。
国外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改编,既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话域外文明的努力与能力,也考验着我们坚守自身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因此,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本土化改编,都要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精神的构建。鲁迅提倡“拿来”之后要“有辨别”,然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由于文化和国情的差异,有些在国外反响不错的作品,对中国观众而言未必合适。如有的作品在鼓励人们摆脱家庭束缚、社会偏见等惯性力量,释放自我、追求自由的同时,却忽视了“自由”和“自我”的边界,与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集体主义观念和家庭道德等产生冲突。这种水土不服的价值观,显然是本土化改编时应当审慎辨别、自觉摒弃的。
即使已广泛流传的经典作品,其本土化也常会面临因文化和时代差异造成的观念冲突。例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一毛不拔的犹太富翁夏洛克成为反面角色并受到嘲笑和压迫,相当程度是因为种族主义和宗教偏见。在当今的中国观众看来,他是个受害者,从他的角度来看,这部戏剧就是个悲剧。这显然与莎翁的原意相违背。如何在尊重经典与本土化之间巧妙取舍,获得平衡?创作者仍需不断探索。
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舞台艺术应当放眼世界,立足中国,以开放的胸怀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以敏锐的识见、充溢的才情,将之转化为富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质精神食粮,承担起传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任,弘扬中华文化、凝聚中国力量。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7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