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商隐到胡兰成与张爱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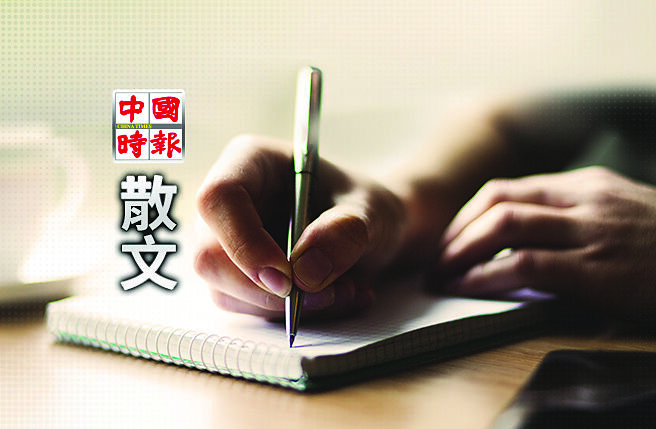
散文
有一位文友推崇胡兰成的礼乐文化说,问我看法,我想了想,表示不管对于前贤或前嫌,自己一向都不敢轻易评骘。但他不死心,一直追问,我姑且这么说吧!提起胡兰成,不免让我想起晚唐的李商隐,他们俩都是有才情之人,唯公私两德可能都有所亏缺。如李商隐为自身官场出路,投靠了自己恩人的政敌,而胡兰成则投靠了汪精卫政权……。又李商隐和胡兰成两人都有某种人格、性情扭曲的自恋。李商隐〈别智元法师〉:「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另一首〈荆门西下〉诗末有:「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诗中尤其是「东西南北皆垂泪」、「却羡杨朱泣路歧」两句,很能把他自己那分自恋者的困境抛露出来。龚鹏程早年有篇〈李商隐与佛教〉一文里,推衍李商隐的苦痛非在歧路而泣的抉择困境,却在其根本无路可走。龚鹏程所见大致可信,但「无路可走」如指其心灵层次的领悟,实则或许未必。李商隐对于自己的困境或「追寻」,这一切,终究都源于对自我蒙昧的执恋。李商隐八岁失怙,十二岁即外出做文书、杂役等工作,日后又卷入牛、李党争。他先是依投牛派的令狐绹,后又娶了李派的王茂元之女为妻,李商隐夹在两个党派中间,备受倾轧。他被时人视为墙头草,「诡薄无行」之人。不知不觉中,自我防卫机制使他把对生命的经营重心转而投注在「自我」之上,即表现为一种畸形的「自恋」。对于一个自恋者而言,在一个深层的经验水平上,他感到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做为自身的镜像才有意义。李商隐某些无题诗,极可能并无摩写对象,或外在对象只是幌子,他摩写的无非是自我美化的抒情,或说是抒情之美化的自我。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一般是赞扬贤人的哲思敏求,但何尝不可开解为人的蒙昧愚行?李商隐或竟耽溺在杨朱的歧路景境。他表面悲伤,实则或竟欣喜于这分「无路可走」;无路可走,他才能给自己一个自我美化的抒情,或说是抒情之美化的自我,他才能且歌且走,且走且狂。李商隐一首写给某名妓的无题诗,其中有句话是:「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诗既赠人又兼写己,其曲折的幽隐约莫如此,而「惆怅是清狂」正抛露出其性格的变异。
现在说胡兰成。性格的养成或型塑,时而隐藏在人世时间流程的迷雾里,但胡兰成性格的扭曲,想至少有一部分得自其年轻时代恋慕的庶母,其庶母扭曲的性格竟浸润、感染到胡兰成身上。早年被一再转卖为妾、命运乖舛的庶母,越年长反倒越发乖戾。胡兰成元配玉凤病危,他回庶母家借钱,庶母不肯借,最后逼急了,他自己打开钱柜,拿了六十元。庶母说了一句:「到底还是我被打败了。」眼眶一红,嗓子也变了。「到底还是我被打败了。」这句话彻底暴露出她那几近变态的自我。
胡兰成在庶母家连住三天,等拿到钱回家,妻子已经病亡。日后胡兰成却这样子自况自解:「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我皆会突然有个解脱,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又说:「人世的吉祥安稳,倒是因为每每被打破,所以才如天地未济,而不是一件既成的艺术品。」
这番话,一般人听来,怕是要不寒而栗的。
提到胡兰成,就不得不提到张爱玲,张爱玲和胡兰成两人有某种原始的相濡以沫的联结或说曲径通幽。其后,张爱玲写小说,有时会把看似相互敌对的两人,写成合体的一人。譬如〈色.戒〉里的男女主角,王佳芝和易先生,以其道德结构看,即可视为同一人。王佳芝来到个人自由抉择和社会共有价值的一个分岔口,依社会共有价值伦理,王佳芝不应该放过易先生这个汉奸,依个人自由抉择,王佳芝不管作了何种选择,关键在于她是不是真的作了自由选择,而不在于她选择了什么?换言之,只要她真的选择了,她就具备道德的正当性。这是第一重检证。第二重检证是,王佳芝所谓的自由抉择,到底有没有可能落在如《自由与奴役》一书的贝叶德夫所说的那种「自我中心主义」式的虚假的自由──这种自我中心主义者,自以为作了自由选择,其实仍陷溺另一种自我奴役的桎梏里。
第一重检证是王佳芝果真作了自由抉择?答案是肯定的。王佳芝决定弃团体职责而就一己私情,而且此一决定如此当下,如此不由分说、迅如电光石火,足以衬映、隐喻其强烈及真实。第二重检证是,王佳芝此项抉择是否源自一种自我中心主义作祟?貌似自由实则奴役?答案居然也是对的。理由是,促使王佳芝决定纵放易先生的,只在于她认定眼前这人爱上了自己这点。而这分认定的真象,至少从某一层面看是扭曲而虚荣的。王佳芝性格原本就有虚荣的一面,学生时代舞台剧公演,下了台,她兴奋得和两个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霓虹灯意象是虚荣的表征。假如这暗示还不够,张爱玲在王佳芝首度色诱易先生成功时,又把她那易受虚荣表象挟持的心智状态再一次抛露在读者眼前,「一次空前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虚荣自是一种感情的扭曲、扭曲的感情。但把王佳芝和易先生两人,都自以为对方爱着自己的那种人格的扭曲,表现到极致的,应属易先生在下令枪毙王佳芝等一伙人后的内心独白,把两人彼此的关系比拟成「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是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张爱玲把这种心灵扭曲表达得同样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前面我们说张爱玲〈色.戒〉里的男女主角,王佳芝和易先生,以其道德结构看,可视为同一人,在现实界,张爱玲和胡兰成的道德结构关系,毋宁也是同一人。
〈色.戒〉小说里,易先生杀了王佳芝后,心想「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使人不由联想起张爱玲和胡兰成那段既不堪又轰轰烈烈的爱情及婚姻。戴柏斯在《性欲、权力、恶行与微笑》书中说:「身上没有伤疤的女人,一定有个软弱或不关心她的丈夫。」这句话在讲什么呢?在讲某个社会、文化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暴力式的浪漫。亚马逊河流域有一个雅诺玛摩部落,该部落女性经常被自己丈夫所伤害,这些女性会自豪地相互炫耀自己身上的伤疤。对雅诺玛摩人而言,热情和暴力没有分别。
张爱玲对薄情寡义的胡兰成,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暴力的浪漫,或说浪漫的暴力。坏男人容易吸引好女人──相对的,坏女人容易吸引好男人。戴柏斯从身心医学来解剖、从人的睾固酮演化的观点来看这令人惊悚的一面;医学研究显示相似的人会彼此吸引。原来张爱玲就是女的胡兰成,而胡兰成就是男的张爱玲。直言之,这是生物睾固酮的角色扮演游戏。在〈色.戒〉小说里连着几句话都表白得很经典:「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级的占有。」
俄裔美籍作家纳布可夫有一部中篇小说《黑暗笑声》,故事题材是《罗莉塔》的另一个翻版,都是讲中年男人对小妖精的迷恋,那分令人叹息的迷执,无非也就是另一种暴力的浪漫,或说浪漫的暴力。
黑暗中,永远少不了有吃吃笑声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