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在风里── 读林仙龙诗集《走走停停;诗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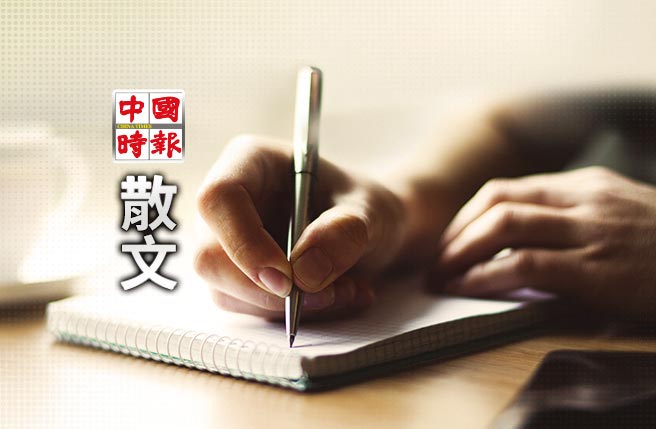
其实很早以前就在报刊杂志读过林仙龙前辈的诗文,但初次见面却是去年五月在他的故乡台南佳里。那时我刚出版《阳台上的手风琴》散文集,突发奇想舍弃既有模式的新书发表会,改以读书会的方式。我不打算在台北举办,而是浪漫的设想一个场景:纯朴的乡镇,雅致的地方,大家围坐在一起读一本书,分享心得或朗读篇章,彼时树影投映窗上在微风中摇曳……于是我想到住在佳里的好友锦妙开的羽侬蔬食馆。那是一场温馨的读书分享会,住在南部数十年未见的同学与友人赶来相会,也认识了许多美好的新朋友,林仙龙伉俪(其夫人周梅春也是散文小说作家)亦从高雄回到家乡参与这场读书会,夫妇俩留给我极为亲切温厚的印象。
今年春天林仙龙前辈出版了诗集《走走停停;诗知道》,书中还对照着李为尧教授的英文翻译。读林仙龙的诗如他的人一般,平淡内敛中自有真味。他以淡笔描写生活,不刻意说什么,却又说出了什么,让人不自觉地沉吟于他自然流露出的诗意中。诗人曾谦虚的说:「做不成伟大的诗人,我就守住自己的平凡,写一点平凡的诗。我喜欢诗丰富的意涵与悠远,我喜欢诗的一股幽微和气味,也喜欢写诗的那一份真趣和自然。」相较于时下许多刻意营造意象晦涩的诗作来说,我以为林仙龙作品的自然恬淡更具诗意,那是一种时时自我省察,发自真诚生命深处,从生活中流出的轻歌──
诗人的作品里常常出现山、海及树的意象,他虽谦称自己平凡,但观其在〈山〉一诗中,如此写着:「站着/你是一座高大耸拔的山岭/站着。你是高山/如果我也要成为一座高山/让心头的岩浆迸出/让身上的风霜覆盖//站着/站成天地的高度/站着。如果我们仍有坚持//……你是高山吗/我是高山吗 」,流露出诗人不平凡的心志,坚毅沉稳、耸立雄伟的高山,是诗人一生的仰望,也是自我的期许与坚持,要成为一座山就必须能够勇敢的吐出胸中的块磊,忍受各种环境的磨练;诗集中常出现的「你」,或许正是诗人与另一个「我」的对话吧!在历经现实生活的种种考验之后,诗人俯仰自问,我还是当年的自己吗?「我们」还是高山吗?这是一个不随波逐流者的时时自我警觉。
当然难免也有感伤的时候,在〈山林〉一诗中他说:「把一座山安在草地前/把一座山搁在回忆里/看着削去半边脸的一座/山;站在瘦瘦的背脊上/我是被困的一座山」,诗人说自己老了,他把自己藏起来,在曾经走山,柔肠寸断的山路上;他最后超脱而豁达地告慰自己无需挣扎,天会老地会荒,那颗耀眼的星星终究会消失在山头上,于梦的空隙。而那曾经远离故乡出外打拚的人,在有所成就之后,相对的也失去了许多,午夜梦回,抚今追昔,忍不住溯着熟悉的山路前进,寻找当年的山,当年梦想的自己:「你把年轻的梦种植/也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用一片一片叶子,把许多呓语/包住。把冷冷的面颊淹没/叶子堆得很厚很厚的时候/你的梦里有一座山/醒来是一条上山的/小路//……听说你常在月光下漫步/偶尔回头看叶子伤心的表情/偶尔回过头看一座山/就在星星的旁边」。此时诗人面对逐渐慵懒和蹉跎的黄昏草原,已不能再追逐和奔跑,只能静静的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守望〉薄暮下的一座山。
诗人是盐份地带的农家子弟,也曾是长期服役海上的军人,因此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并不陌生,海的平静与起伏,都化成他内在情绪的涌动,海上有船、有水鸟、有水手,也皆成了诗人诗中的喻依。「大海的情绪很复杂/涨高了又抚平/抚平了又涨高/没有人了解/海涛带来了什么又失去什么/海涛坚持什么或者放弃什么」〈海边印象)。「大海,来。我们坐下来/我们暂且不要喧哗/且看一艘船驶过茫茫的大海/且看一艘船看着远方天际的/满天星斗;像勇敢的海鸥/不断的冒险不断的飞翔」〈水手〉。
至于诗中的树,在本书中占了很重的分量,它是坚韧的生命力、它是母亲、是信仰、是故乡、是大地的守望者。不管是开王殿前有着风雨齿痕,跌倒而又匍匐活过来的木瓜树,结出的一颗颗青木瓜用海口腔说它的苦难与勇气。抑或是从野地、海口移植的苦楝树,它们厮守在铁道旁,看南下北上的列车,看一双鸟儿高飞,留下的是白头翁,是心苦的苦楝。至于那棵拥有自己一片天地的黄槿,开着黄澄澄的花,不动不摇的任由她爱的孩子,蝉儿、金龟子和独角仙等在她身上爬上爬下;而黄昏的炊烟,厨房充满妈妈味道的蒸粿香,挑着重担或在树下赶鸡鸭的妇人;树和妇人都不笨也不累,她们都是十足的母亲。
那曾被孩子攀爬掏蛋、嬉戏的〈海边的树〉,有一天孩子长大了成了浪迹天涯的水手,水手们回来又随着一阵风走了,就像那几番盘旋却从不栖息的海鸥:「都走了。都在远方/都像一棵树/在路边等待;都像一棵树/向海上张望」,树孤零零的站在海边瞭望,每一片叶子都熟悉风涛,都曾经哭泣──「有谁知道日落以后/木麻黄为什么摇着身子/站着;等一只北归的候鸟/等着一盏渔火;在大海上/看无助的一张脸/看你;为什么把许多的过去/都忘了」〈防风林〉;树的身影彷如母亲的身影,那也是来自故乡的呼唤。
由风或鸟带来遗落在野地的一颗种子,于干旱的田地落户的一家农人。种子在贫脊砂砾上生长、抽芽,努力的长成一棵苍翠的树;农夫一家大小,沿着田埂搬运、挑担,孩子沿着田埂上学、长大……悠悠忽忽四十年过去了,农人已离去,牵牛花爬上了农家的屋顶,「风会来/雨会来/虫儿鸟儿会转身回来回到大树上」,对游子来说这〈野地的一棵树〉成了对家对故乡的悬念。于是「满山遍野踩过的步子都成了纷飞的叶子/满山遍野厚大的叶子都循着步声回来/寻找一棵树」〈每一棵树都长高〉。
于是那个曾经离去的人绕过草径,在〈三月的小雨〉中回来了,「一条河醒了/一条河听见流动的声音/一条河听见花开的声音/每一棵树都在山头上等待」,等待那个曾经离去的人岸边回头,在微雨和柳丝里。而看着〈一格一格的盐田〉里那几颗盐粒望着天空发呆,与退休的盐田一起被结束,仍然记得盐的苦涩滋味,晒盐的村子没有人晒盐了,数过一格一格的盐田,这里曾经有盐,这里已经没有盐了,「一棵干枯的树/落光了叶子/一棵干枯的树/张着枝桠/在沉沉的暮色里」,时间不断的往前行,故乡也一点一滴在改变中。
诗人回来了,带着伤,只是看一棵树。站在自己种植的一棵大树前,他突然有了领悟,过大的野心或许也比不上树上一只毛毛虫,他看到一只毛毛虫找到蜕化的理由,在大树前面翩然起舞,生命遂回归最纯真的初心,诗人追寻自己的蜕变。他是农人,他熟知田里长着什么,他和种植的那棵树,安安静静地守住一亩硝薄的盐分地,于是时光转化为一种和煦的光辉,一种熟识的芬芳,繁华纷纷退去,在大地上一锄一锄耕种的诗人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闻到贴近土地宁静朴实的气息。「生活在人间/一棵树懂得伸开它的枝懂得张开它的叶/一棵树比我更早懂得。跨过去/是诗」〈剩下;诗知道〉。
另外〈修剪〉一诗中,诗人虽说是修剪一棵菩提树的枝桠,其实修的正是自己的心性,「我知道祂在看着我/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一把锯子。看一个人/修剪的/模样」,此时菩提树是佛,也是心中最清净庄严的自己。而看过晨光落日,看一个人从海上回来的〈盆栽〉,以青翠的叶子、艳丽的花朵告诉他,他不在的时候她施肥又浇水,她把所有的窗子打开又把窗子全关闭;「还是再种一棵小叶榕/还是再种一盆蔷薇一盆金线菊/我一铲一铲努力的加土填土;她坐在窗前/反复的;反复的说了些什么/她走来浇上一盆水//请记得。请记得/请记得把盆栽摆在向阳的窗台上」。小叶榕四季长青充满生命力,蔷薇代表爱情与思念,而金线菊是善于等待的,诗人借着〈盆栽〉含蓄内敛地传达了夫妻之间的深情。
诗集最末首诗人以〈我回来了吗〉作结,呼应书一开头的〈山〉,也同样都用疑问句:「山。站在前面了吗/山。站在大海的前面吗//……我必需坐在窗前想起这些吗/我必需坐在来回的路途上/回到大海边。回到断崖上/听一声;简单的/呼叫/我回来了吗」。仿佛经过长途跋涉的旅人,站在天地之间,对着悠悠岁月大声呼喊着:「我回来了吗」,这回来是身心的归返,是「我」与「你」的相见欢,诗人以疑问句留下想像的空间,或许诗人是明白的,他知道答案就在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