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万分之一的女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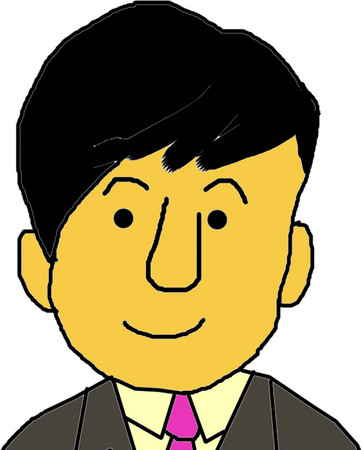
已经多年没连络了。换了新的行动电话后,绘里的号码也没再留下来。所以,她的电话打来时,我望着似曾相识的号码,一时间困惑了一下。
接起电话,几乎就在话机传来第一声的同时,我听出是谁了。
「もしもし、ナル(喂,是Naru吗)?」
听着熟悉的声音,我一怔,思索着该接什么话。
半晌,我回过神,对着电话道:「はい。もしかして、絵里(是的。难道...你是绘里)?」语气迟疑,但心已笃定。
绘里说:「我是绘里。Naru还好吗?」
电话中短短的几句,一下子勾起了几年前和这个女友的总总。
周遭日本同事怂恿下,我抱着姑且一试兼好玩的心理,把自己的资料放到日本的社交网站。
两周后,绘里出现了。
绘里发来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对您的资料感到兴趣。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再多了解您。」
内容中,没有年轻女孩爱用的符号文字,写得四平八稳,短短几行,已经透露出诚意。
看看她的资料。26岁,身高170。首页照片是一张漂亮脸孔。
打开详细内容看,我惊呆了。长腿长发,靠着栏杆的站姿照片。女孩穿着短裙,眼睛很大,身材仿佛模特儿。
「美女呀...。」从来不自言自语的我,也忍不住发出低吟的赞叹。
这样的女孩,会找不到男友?会需要在网上物色对象?收到绘里的「交友请求」,我固然有「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的雀跃,但更多的,还是疑惑。
「谢谢来信。承蒙青睐,感激不尽。我附上常用的email信箱如下xxxx。」
就这样,两人开始频繁地信件往返,我也不再有「男孩子的矜持」(本来也就没有过)。有信必回,没信也回,龟息吐纳也省了。为了怕日文写得不道地,我每写一句,就上网查查有没有现成用例,深怕自己写的东西让日本人笑话。至于那些疑惑:这么好条件的女孩子,犯得着到网上找对象?又为何找上我?就先姑且视做天上掉下来的大礼,「存而不论」。
在日本,工作时间不上网、不收私人信件,是一个常识。而日本人又是个极度严谨的民族,一切按部就班,循序渐进。通了几十封email,只要没进入下一阶段,仍不知对方电话号码或其他联络方式的,毫不稀奇。所以,我们直到见面前,email是我们唯一的联络方式。
我变得喜欢早早回家,收信,写信。再收信、再回信。热度逐渐升级,写信成了甜蜜的日课。
随着她陆续发来的照片,我可以确定:她资料无误,照片即是本人。但对于自己的工作,她则是讳莫如深,只说「到时会告诉我」。
面还没见,留点神秘感不算太过。但把自己的职业视为保持神秘的范围,可说是「崭新」(最近日本流行语)。
她的文学造诣极佳,汉诗也懂。知道她也和我同样住在神奈川县,我心血来潮抄录下《卜算子》的一小段给她: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不久,她回信来了,内容正是这阙《卜算子》的下半段:
「此の水 几れの时か 休み? 此の恨 何れの时か 已まん?只だ 愿はくは 君が心 我が心に 似て、定めて 相思の意に 负かざらんことを」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她接着写道:「我在大学时,选修的正是汉文。刚好读过这篇《卜算子》。看到你发过来的这段,心想:真是巧!就把下半段发给你了。」
感谢老祖宗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让我如今能和这个日本女孩多了一个共通话题。
我告诉她我的工作、背景。我老实承认:由于自己是个外国人,尽管考虑在日本长期生活工作,但若职务调动,离开日本也不无可能。
「任谁和我在一起,都要有心理准备。她可能得随着我东奔西走。」在信中,我这么跟她说。
她回复我:「我早就向往在海外的生活。能和喜欢的人一起出国,是我的梦想。」
「谁会和我在一起」,我没说破;「喜欢的人是谁」,她也不说穿。仍在通信阶段,但是两人想的事情,已经是数年后之远了。连她也承认:「メールでこんなに気持ちが高まると思わなかった(写写email,也能写得这么难分难舍,真是始料未及)!」可以说,我们光是通email,就已经发展出近似情侣般的情愫。
就在电子邮件往返了一个多月,「见面」逐渐变得顺理成章后的一个晚上,我主动提出第二天见面的要求。她爽快地答应了。同时,也告诉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我依照这个电话号码,发了第一个简讯给她:「您好,就要见面了,我们先在电话里聊几句吧!」
五分钟后,她的回复来了:「いいですよ(好呀)!」
我拨通了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了女孩子清脆的声音:「Moshi Moshi...」
「喂,是我。」
「我知道。」
沉默半晌,怯生生的两人,随即不约而地笑了出来。
我们聊开了。我单刀直入问她的工作:「都要见面了,这总可以透露了吧?」
她笑着说:「我们明天不就要见面了吗?到时会告诉你。你先放心:不是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也行。就差一天,没甚么非得要在此时此刻搞清楚一切的理由。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后,我们接着闲聊了一个小时,最后,带着满足的心情,愉快地挂上电话。
约会当天,我刻意把手边的工作提早做完,从东京搭「田园都市线」,再转车赶到横滨站约会的地点。约定的晚上7点,我准时到,她则稍迟了10分钟,途中猛打电话道歉。我的准时让她觉得这么内疚,我反而因此有些自责了。
没多久,绘里,这个和我神交一个多月的女孩子出现了。大冬天,她留着直的头发,穿着长裤马靴,看来比照片中还高挑亮丽。照片全无加工,让我放心不少。她深深鞠了一个躬,为了自己的迟到,嘴上止不住地连说「失礼」。
我笑着说:「快别这样了!你再道歉下去,我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们走到附近一家中国料理,坐定,点完菜后,两人开始了首次面对面的聊天。她主动提起了自己的工作。
「我其实是做模特儿的。老家是在青森县。在青森时,走在路上被经纪公司的人相中,就到了东京做起模特儿。但是,是杂志、宣传广告的平面模特儿。我的身高还不能站在伸展台呢,」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之前没提我的工作,就怕你知道后,会对我有不当的联想。要不就是想得太坏,要不就是想得太好。」
我一怔,追问她:「为甚么?」
「想得太坏,认为做模特儿的,生活一定很糜烂;想得太好,认为我一定是大美女。我两个都不是。只是个普通人。」她苦笑道。
绘里生活糜烂与否,我还不知道;但眼前的她,确实是个美女,她的美貌是毫无疑问的。
如今她亲口说明自己的工作,这一个多月来最大疑惑,就此解开。她端起杯子,啜一口茶,优雅地让我自惭形秽。她是吃这行饭的,每一个动作都看似训练有素。这样的女孩,看得上我吗,一个只是在东京混生活的外国人、普通上班族?
「网上对象这么多,你怎么选上我?」我忍不住问道。
她答道:「恩….第一,你照片比较正规,不像别人,随便拿着手机、拍个45度俯角的照片就上传上去。这一点看来,你是很认真的人。」
原来,这也是女孩子挑对象的重点之一。
她接着说:「你会讲外国话,我很羡慕。我想从你这里多学点东西。」
这也听来合理。女孩子崇拜有特殊才华的男人,古有明训,斑斑可考。
「这两点就让你选中我?」我意犹未尽地问道。
「另外,就是你…,」她突然噗嗤地笑了出来:「什么叫做『光合作用』呀?。」
我听了,愣了半晌,总算会意,大笑 。绘里说的是我在网上的自我介绍:「闲暇时,喜欢在室内进行光合作用」。
正经的相片、会外语,再加一点亦庄亦谐的自我介绍,我打败了网上诸多更优秀男士。
菜一道一道上来,但吃饭已经不是重点。我们聊得很开心。我爱爵士乐,绘里也爱;绘里爱文学,我也爱;两人话匣子打开来就说个不停。一餐饭,一直吃到九点半,店家提醒我们即将打烊,我们不得不走。
出了店外,店内相谈甚欢,心中余韵仍在。我看着身边的绘里,她脸上的表情,似乎也有一些不舍。
「我看你脸上表情,似乎有些不舍...」我想到什么说什么,说得绘里呆站在原地,应了一声:「はぁ~(啥)!」脸上好气又好笑。
「是你不舍吧?」她说。
「我不想与你争辩这点小事」我故意正色道:「我们到樱木町吧!那里的Landmark Tower顶上,有个酒吧,开到很晚。明天反正周六,我们去欣赏夜景吧。」
我们从横滨地下铁站,搭到樱木町,穿过联络道,坐电梯直上LandMark Tower 70楼的酒吧。
服务生领我们到面对横滨港的窗边座位。我们面对着港边Clock21的摩天轮,坐下。点了两杯饮料之后,两人看着港边灯火罗布,开始闲聊。摩天轮闪烁着霓虹灯,把绘里本来就立体感十足的脸庞,照得玲珑有致。
「为了你,我上网查了『台湾男人』,」绘里说:「你知道网上怎么评论吗?说台湾男人是『亚洲的义大利人』,很会谈恋爱!」
「ええ?そんなの初耳(咦?第一次听说)!」这话,未知褒贬,若是褒义,那我就真要感谢筚路蓝缕,为台湾男人在日本建立美名的同胞前辈。
我们有的没的,谈了两个小时,谈到一对对情侣纷纷买单离去,这才准备离开。
「等一下,」绘里边说边伸出手来,帮我把脖子上的围巾拉开卸下,顺好了毛,再帮我围上。她轻拍我的围巾,端详打量了一番,似乎很满意自己的巧手,说:「外头冷,这样围才保暖。」
「确实,这样是暖些。」我回答。其实更想说的是:心里的感觉更暖。
走到出口电梯门前,不知何时起,两人牵起了手。
「这算是开始交往了,对吧?」我看着她,问道。水到渠成如斯,我仍希望她一句口头确认。
她点点头,有些娇羞地回复:「はい(是的)」。
日本计程车资不低,但为了多一点时间与她独处,我还是叫了一部车,送绘里到横滨「关内驿」她的住处。车窗外的景色如走马灯般一幕一幕闪过,两人一路无话,但我依稀记得她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接近她住家附近时,她说在家附近的便利店下车即可。她想买些明天的早餐。
「那,小心点!到家记得发个简讯给我。」我在车上挥挥手,向她告别。
车子开走没多远,从后车窗看着她的身影走进便利店,我心里突生一计。我要司机让我就近下车,付了车资,狂奔到便利店附近,站在门旁边,偷偷守候她出来。
绘里出来,往隔壁巷子里走,没发现我。
我蹑手蹑脚走到她身后,喊了她的名字:「绘里!」
「啊!吓一跳,Naru!」她又惊又喜地看着站在身后的我,两人笑闹了一阵子。
这一段在巷子口的嘻闹,据绘里事后告诉我,那是她最难忘的一幕。「日本人の男はそんなことしないから(日本男人就是不会这些)。」绘里每每跟我回想起来,总要奚落自己同胞一次。
我正准备转身离去,绘里突然问:「一绪に部屋でお茶でもしませんか(要不要上来再喝杯茶)?」我没有进她房间的心理准备。对这突如其来的邀约,我稍稍迟疑了一下,才说:「はい(好的)!」
我们搭电梯上了房间,进了屋内后把外衣褪去,挂在沙发椅背上。日本租屋,一般不许租客张贴悬挂任何饰物,房间四壁萧然,但桌上、架子上别有洞天。爵士乐手Miles Davis的照片摆放在桌上。架子上则是绘里亲手绘制的油画,还有两三张她的模特儿独照。
绘里打开落地窗,为阳台上的小花盆浇完水后,回房,把暖气打开,泡好茶,为我倒满一杯后,打开音乐,把一本相册翻出来。
「若い顷のお父さん。恰好よかったんでしょう(这是我爸爸。年轻时的他,很帅吧)?」绘里边翻相册边说。我看着一张张甜蜜的父女合照,觉得绘里初次见面就向我展示家族照片。她对我们的交往是认真看待的。
我们在房间コタツ(带暖炉的小方桌)边上坐着,翻着相本,听着音乐。偶有消防车经过,而我俩心波不惊。
当晚,我睡在她的房间,手臂枕着她的头,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周六的早上。
我在横滨,绘里的房间,外头或者刮着冷冽的寒风,或者出着温暖的冬阳。不知道,也不重要。眼睛尚未睁开,已经仿佛闻到绘里的发香,和依稀飘来的、女孩子房间特有的味道。我肯定昨晚的一切,究竟不是梦。我睁开了眼。绘里躺在床上,背影对着我。我伸出手,才一碰到她的头发,她即转过头,看着我,四目相对,两人同时笑了:「おはよう(早安)!」
我一只手臂绕过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抚摸着她,两手把她环抱着。她蜷曲着她的腿,勾着我的腿。两人无话。此时无声胜有声。
半晌,她像是想起什么,突然转身问我:「ねえねえ、気になるんだけど、休みの时光合成するってマジ(恩,我很好奇,你休闲时真的会做光合作用)?」
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她这么认真看待。我促狭地说:「当然。家里摆了盆栽,和盆栽一起做!」边说,边指着窗帘缝隐隐透出的光源:「这是中医理论。身上哪里想长,朝着阳光处作光合作用,就会长了…。」
绘里瞪大了眼睛,好奇地问:「真的?」
「真的。你昨晚没领教?」我说完,故作神秘貌。只见她脸上表情从惊讶,到娇羞,再到微笑。最后,她好气又好笑地说:「你的黄笑话,要人花时间才懂!」
两人温存片刻,绘里起身,穿好上衣,用遥控器把暖房电源打开,掀开窗帘打开窗,看着阳台的小花盆,像个孩子般地说了一句:「アァ~、爽やかな朝だわ(啊,真是神清气爽的早晨)!」。
窗外的阳光,把绘里的影子照到地板,拖得好长。我也起身走向她。地板的影子叠成两重。
「早上吃什么?你在便利店买的早餐,大概只够一人吃吧。不如我们到外面吃吧?」我抱着她,问道。
她说好。稍稍补了一点口红,和我穿戴整齐后,绘里带我到住家附近的「家庭餐厅」(ファミレス)吃早饭。她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谈着自己的身家背景。
「爸爸是外交官,公务员。小的时候,我们曾跟着爸爸到美国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年纪太小,我英语全忘了。」
「爸爸死时,我才念小学五年级。我们一家回到妈妈青森县的娘家。生活重担全落在妈妈一个人身上。家里过得很清苦。一句话:就是『穷』。」
「我小时候,个子就比其他的孩子长得高,身分是『归国子女』,又没了爸爸,家里没钱,青森方言也说不好,很受歧视。同学老爱叫我『长颈鹿』,我为了这个,小时候总是闷闷不乐。」
「长大后,有个梦想,希望能离开日本,到别的国家过日子。我不喜欢日本、不喜欢日本人。和Naru通信时,偶尔会幻想:Naru懂得外国话,要是认识了Naru,Naru带着我出国,我会好开心。」
我静静地听着她说。她像个孩子般,寻找一个可依赖的人。看来,她把我视为「那个可依赖的人」。
她继续说:「日本景气不好。我大学毕业后,没做过正社员(正职),都是做派遣员工。直到被经纪公司相中,才做起模特儿。」
「别看模特儿光鲜亮丽,其实是有一顿没一顿。我做的又是平面模特儿,景气不好时,赚的钱比派遣员工都低,其实很可怜。」
绘里看来体面的外表下,人生路走得并不顺遂。比较起她来,我算是没吃到什么苦头,家里不算富有,但是健全,留学领的是奖学金。就职以来,薪资越领越高,可用一帆风顺来形容。跨着海洋、隔着国界,两个人走过这么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如今也走到了一起。我不知道我此时出现,是「适得其时」,还是「相见恨晚」。
「唉,可惜自己没能早些参与妳的人生呀,」我说着。只是没吃过苦的我,面对吃足苦头的她,我连说这话的底气都嫌不足。看着她的表情,我知道我说错话了。
她苦笑了一下:「你就算早出现,也什么都不能改变呀。」
我们吃完早餐,绘里坚持要付账。我想,来日方长,总有下一餐、下下一餐,我付她付都不是重点。
我已经开始思考:我会带绘里走,圆她的梦,我若真爱她,这才是我该为她做的。
我们走出店外,我刻意放慢脚步,让她走在前面,端详着她的身影。她好美,让我多年以后的今天,仍深刻记得她那时走路的姿态。
但多年以前的我,只看得到浅处,看不到深处。绘里在早餐店里的一席话,已经暗藏了我们日后分手的伏笔。
第一次的约会,比预计多了一夜又一天。从此我们发展成稳定的情侣关系。假日,她只要没接模特儿案子,我们就到东京或近郊约会。涩谷道玄坂上的一家名为「狮子」的爵士乐咖啡厅,是两人爱去的地方。日本情侣不习惯并排坐着,觉得在人前亲暱有失体统。我和绘里,一台一日,不管别人眼光,绘里就坐在我旁边,我就让绘里倚偎着。记不清有多少个午后,在Miles Davis的乐声中,我和绘里坐在咖啡厅昏暗灯光下的一角,她靠着我的肩头睡着。当时的我,满脑的幸福快乐,想着:「如果人间有天堂,这里就是天堂;如果人生有极乐,此刻就是极乐。」
绘里的性格有独特的地方,她不像其他日本女孩子般内敛,相反地,她非常乐天,接触到她的朋友们,很容易感染到她的开朗。我和她,说起来像是日本漫才(相声)里的「ボケ(装傻逗垠)」和「ツコミ(吐槽捧垠)」,我说话傻,她说话机伶,我们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还记得那天公司聚餐,绘里刚好也有空,我带着绘里,首次介绍给在场的同事。她劈头第一句话,竟是「どうも、ナルのセフレです。(大家好,我是Naru的性伴侣!)」说得在场日本女同事和我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得干笑了几声。等到聊开了,绘里立刻成了众人的开心果,和这些女同事混得比我还熟。
一个长辈级的男同事,平日温文尔雅,那晚大概是喝多了酒,居然拉着绘里说:「日本男人有啥不好?日本男人的那话儿(チン棒)可长了呢!」
尽管出言不逊,绘里居然也四两拨千金:「是吗?人家那话儿可有四千年历史啰(*),你多久?」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日本一般认知中国为四千年历史)
本文下篇--六十万分之一的女孩(下)
●作者老侯,硕毕,在日本谋生的台湾上班族。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ET论坛欢迎更多声音与讨论,来稿请寄editor@ettoday.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