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出一条回家的路──陈家带诗集《火山口的音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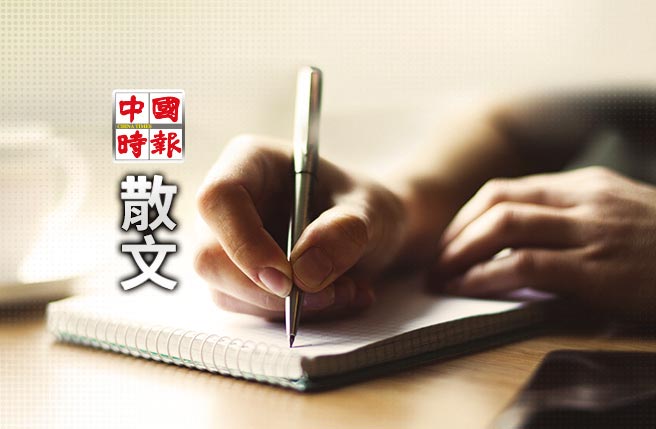
散文
诗是宇宙潜意识在人身上的展现形式,诗的生发绝非偶然,必是遍在宇宙各个深处角落的。每个人都似独立的一颗星球,不知为什么地绕着一个黑暗中心旋转,内在都充满了能量,却可能一辈子都忘记向外喷发,诗人是耐不住这种骚动的。而骚动的骚字拆开来看,或指马匹耐不住搔痒,内在涵义说的正是一种被压抑的情绪无法忍耐后的行为表现,如此诗人之所以会被叫骚客也就不足为奇。「深闺幽怨,骚客工愁」,诗人的愁正是内在压不住的能量时不时要向外喷发。仰望夜空,浩瀚星海,有光处必有无数行星饱含火山想要喷或正在喷,而恒星或像是彻底炸裂解放至极致而不可收拾的火山。
陈家带在漫长的「诗的火山岁月」中则是极为随心、随性乃至随缘的,有时想起「火山口的音乐」了,就向外喷一阵子,更多的日子几乎是休眠的状态,玩一玩他的黑胶唱片,举起紫砂小嘴壶冲倒他的铁观音茶,要不吆喝着旅行考察去了,像极了他的故乡基隆,后来就常常忘记了下雨,而年轻时的基隆那可是全世界的雨都会下在同一个黑色屋顶上的。
当他还是二十多岁的啷当青春,当七十、八十年代诗人辈出时,他即以一首代表作〈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顶〉崛起诗坛,才一出手即鹤鸣鸡群,谱出了自己年轻特异的声音,比如这样的段落:「我听见轻快的雨声中载负几分重量/我看见华美的雨光中含带几抹凄凉//我知道雨是孤独削瘦的/被天体分割被地磁引诱/我知道雨是静默神秘的/被全世界发光的事物欢呼着//春天使得黑暗也开始流动的时候/我看见全世界的雨落在同一个屋顶上」,如此丰美的意象、流动着音乐声响的诗句,在那年代绝对是独特而令人神怡向往的,此后传诵多时,被晚出的诗人赞扬有加,誉为具有「最高湿意」(鲸向海语)的佳作。
只可惜他在1975年出版《夜奔》、1980年出版《雨落在全世界的屋顶》后,诗名正盛,却隐伏沉寂了近二十年,间有零星诗作,要到1999年才再出版《城市的灵魂》一书。之后又再度如「火山口的音乐」暂时休眠去了,到2008年才听说他以一首〈铁观音在我身体旅行〉荣获台北文学奖现代诗首奖,那时他已年过半百,而且在简介中预告即将出版诗集《春天不会偷工减料》,却始终未见到此书,要到2011年才见到诗集《人工夜莺》问世。如此或可看出他随心又随缘、不随潮流起伏的个人特质,果然如孤立荒野的一座火山,想喷才喷、欲火才火,在2008年的简介他还自谓「喜欢美好纯粹的事物,例如印象派音乐、新浪潮电影,还有火候独特的猫空铁观音茶。于诗深爱王维的高淡,也欣赏李商隐的深幽。」高淡、深幽正说明了他的诗观,恐也是人生观。其后他的「喷发」趋于常态,2015年出版《圣棱线》,接着即是眼前这本《火山口的音乐》了。
对「美好纯粹的事物」偏好,说明了陈家带的「洁癖」,但这世界偏偏所有事物都掺了很多杂质,甚至是恶浊不堪的,由此必生矛盾纠结。但作为新闻专业、记者出身的陈家带,基于本业专长,又有为民发声的天职,很自然地会对所处环境和世局、乃至对现代文明、自然生态的迁变,有深刻入微的观察,相对于常人,有更深切的记录、思索和体会,刚好可借助左右身边的媒体刊物代为传播,如此其骚其忧不必然再以诗艺传达,这或可解释他休眠期偏长的原因。但新闻讲究真实和批判,这毕竟离他喜好的「美好纯粹」有不短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于是内在骚动依然,那又当如何「离其骚」或「离其忧」?这又可能使他想起离群孤立荒凉的「火山口音乐」了。他的新闻专业是「即」,他的火山口是「离」,除了音乐和茶,他的诗于是成了我们还看得见的陈家带展现「美好纯粹」的一面,那是他将世界「提纯」的方式。
从《火山口的音乐》四辑的分类或可约略见出他「提纯自身」的策略,辑一「在地平线外」是地、辑三「镜面折射中」是人、辑四「天问的形式」是天,辑二「灵光再现」接近诗艺神秘之源,可视为神,四辑刚好是海德格「天/地/人/神」四重说的领域,而「神」正足以抵挡被非本真化、并试图重建的「天/地/人」,使之回归正轨。
辑一「在地平线外」多歌咏台湾地景地貌,深怕它们日渐消亡,乃有如〈黑琵中请勿打扰〉中说:「水面最痛的倒影/不断不断啄着我底心/苍天的零码杰作/骨立形销/HAPPY中/请勿打扰」,HAPPY跟「黑琵」成了同音同义词,却有可能遭到惊扰,诗人为此担忧而提出呼吁,即使呼吁没什么用。
辑二「灵光再现」则是他平日玩赏文学艺术的感怀和心得,兼向心仪的古今艺术家致敬,诗有曹操、曹植父子,小说家有曹雪芹、白先勇,音乐最多,从莫札特、萧邦、布拉姆斯、德布西、史特拉汶斯基、到盖希文、约翰凯吉,此外还有普普艺术的开创者安迪沃荷等。
辑三「镜面折射中」或书写尘世景象或对自我身处其间的对应/脱离方式,依旧充满声音的元素,比如〈火山口的音乐〉、〈某个失联的夏日〉等均可观察。
辑四「天问的形式」涉及了天道中玄之又玄不可尽解的「幽明之惑,永恒之叹」,涉及三段四论五行等形式,或有永劫回归的玄奥隐藏其中。楚国屈原曾作〈天问〉,问了一百七十多个没有古人可帮忙回答的问题:「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日月阴阳如何而来谁使之生?天有九重谁能度量?如此大的工程谁来完成?屈原几乎是多疑的天文学家了。陈家带则透过各种诗形式的实验来提出他的天问,因此本辑在形式的变化和生命内容的疑惑和提问也最多。压轴一诗〈世界的冠冕〉行数最长,又分〈人:曙光之子〉、〈地:水火的祝福〉、〈天:万有之门〉三部分,「冠冕」二字也隐喻了孤立天际的火山,试图贯串缩影此诗集原四辑精神,有现实、有批判、有玄想,企图心可谓不小,唯说理略强、语言和意象稍稍跟不上。
陈家带对「美好纯粹的事物」的偏好充分展现在这本《火山口的音乐》中,不论分辑和诗作的形式和内容,都说明了诗的纯粹是他的「洁癖之最」,唯如此方能如火山自深层地心喷向火山口并直上九霄云天,将内在能量化成浆成灰成尘成烟成音成乐成无乃至无所不在,完成「天问」的形式,自由穿梭于天地人神之间,诗出一条回家的路,如巴什拉说的达至「一种宇宙性的死亡」,而这何尝不正也是「一种宇宙性的重生」?
如此,当陈家带说「天问,即诗的完美形式」(〈世界的冠冕〉)时,说的即是每当火山口奏出音乐,都是以最激昂纯粹、不顾一切的力道仰口向上「天问」,意即以灰以烟走向死、又发出惊天交响走向生,读陈家带的诗时也当如是观察和冥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