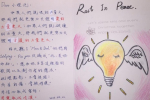丁稳胜/小灯泡妈妈的那条艰难道路

▲失去了小灯泡,小灯泡妈妈走上一条可告慰女儿在天之灵的路,注视被告成长史与疾病史,找出犯行重大机转的原因,并请求政府提出对策。(图/镜周刊)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凶手行凶的被害人,小灯泡妈妈王婉谕在案发后迅速得到社会舆论及各种立场人士的深切关怀,她的一言一行势必牵动着整体国民的思绪,因此,就在各界摒息聆听案发后被害者妈妈的首发谈话时,妈妈的发言令多数乡民疑惑,为何第一时间好像在替被告说话?
事实上,那是她在剧痛之余告诉大家,这件悲剧或许事出有因,而找到原因与真相,才能对小灯泡的牺牲有所交代。从此之后,她走上了一条最艰辛的道路,一条她认为唯一能告慰小灯泡在天之灵的路,注视被告成长史与疾病史,找出犯行重大机转的原因,并请求政府提出对策。
即便乡民在不暸解案情的状况下,对她提出各种质疑甚至污蔑,她都逆来顺受,温和坚定地走在一开始她就决定的道路上。这种特殊的悲痛遭遇与事后反应,不管在法律、社会、心理、医疗等领域,都是一个非常突出且值得关注追踪的特殊个案。就我接触的各方专家,几乎一致地认为婉谕在案后的言行举止是十足可贵并让人敬佩的。
我,做为一个近距离陪伴的告诉代理人,一个死刑怀疑论者,自以为相当快速进入婉谕的思维脉络中,从侦查到二审、程序外的修复式司法程序乃至司改国是会议,一路相随。然而,在一个修复式司法协商会议的午后,在她与大经频频拭泪述及案发当日的事实后,我回到家中,看到自己的儿子,我突然悲从中来,崩溃大哭。
我,只是单纯想像今天失去至亲的人是我,就手足无措了,我根本无法完全设身处地去理解及感受她的剧痛。诚实说,我根本不敢逼近它。也因此,我无法真正理解在此剧痛之后,婉谕凭借着什么力量,在每天悲伤拭泪的同时,还要用冷静理性武装自己与社会对话,这到底需要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
从那些与她互动中感受到的生命质地与个性,婉谕是个让人喜爱的女性,或许她本来就是一个温柔平和且好思辨的女性。然而,在这场灾祸之后,她与先生一样,面临生活剧烈变调的冲击。面对多方社会支持,她心怀感激。但事实上,对于永远的失去,不只难以释怀,而是根本无法放下。我们,告诉代理人,都知道。
我忆及我的伙伴李荃和律师在脸书上曾写过那么一个故事,述说的是他的梦境。梦中,支持废死的他,子女遭杀害,他竟然担任被告的辩护人(梦中没有严谨逻辑及回避问题),在开庭时他慷慨陈词从两公约、宪法人权保障讲到刑法责任能力。庭后,他竟手刃凶手,杀了他的当事人。醒来,他发现自己泪湿襟衫。
这篇贴文震撼我许久,即便是支持废死理念的法律人,一旦试着站在被害人位置时,就无法避免镇日周旋在悲痛、仇恨、愤怒、后悔、失落、自责……等负面情绪中。
许多人率断认为,小灯泡妈妈因为太过讲求注视被告而自失立场,所以对量刑也不会有强烈的意见。但在最终讨论量刑意见时,我永远记得婉谕说:
积极的防治此类犯罪的滋生,是我在小灯泡逝去中努力找到的意义;而我也尚未认同或支持废死。只是,本案判死真的没有办法缓解我的悲伤,我只希望他不会有再害人的机会。对于量刑,我基本尊重合议庭基于法律的专业判断。但因为家人是一辈子的,也是最重要的,我支持我先生关于求处最重刑罚的意见。
罪与罚(定罪与刑罚),有其各类社会功能与需要。但在法庭活动之外,无论之于诉讼当事人本人或者其家属,还必须面对无止尽的情感纠葛与人性挣扎,从没有轻易解除伤痛的刑罚方案。
我们支持小灯泡妈妈,不在于期待她个人的超越,为我们一肩扛起进而换得终局的解答方向。一个社会机制的失灵,你我都是当事人,都应该做点什么,这是我们能给小灯泡妈妈的真正支持。(本文经作者同意转载,原文刊登于PNN公视新闻议题中心)
●丁稳胜,律师,小灯泡案件告诉代理人。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